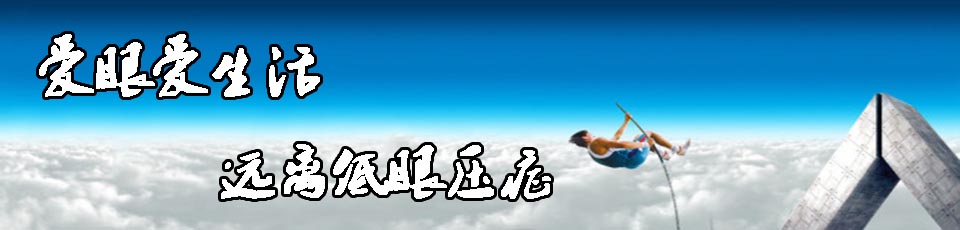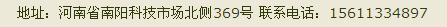高强度聚焦超声在青光眼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本文原载于《中华眼科杂志》年第1期
超声波是振动频率高于20kHz,超出人耳听域的声波。超声波的发现,可以追溯到年意大利生理学家Spallanzani的蝙蝠实验[1]。年,法国物理学家PaulLangevin及俄国发明家ConstantinChilowsky共同提交了一个基于超声的潜艇探测技术的专利申请,这是主动式声呐系统的雏形,也被认为是超声技术应用的起源[2]。之后直到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1名神经精神病专科医师Dussik[3]发表了1篇应用超声技术对人类脑室进行成像的论文,超声才被首次应用于医学领域。虽然该研究结果存在一些争议,但这篇学术论文是超声作为诊断工具应用于医学的最早记录。与此同时,在医学领域,除了超声影像诊断技术的发展,超声技术还被首次应用于脑部疾病的治疗[4,5,6]。当足够的超声能量聚焦于机体内某个治疗靶区时,超声产生的热量可以使治疗区域内的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同时,治疗过程中对处于聚焦治疗区域外的组织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小的影响,且超声对非透明组织具有一定的穿透能力,因此治疗性超声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对组织具有选择性的非侵入性的治疗方式。这种技术被命名为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intensityfocusedultrasound,HIFU)。随着成像及定位技术的发展,HIFU技术在临床应用中逐渐得到推广,尤其在实体良性和恶性肿瘤及眼科疾病的治疗领域。当前,HIFU在眼科中主要被应用于青光眼的降眼压治疗。本文将对HIFU在青光眼应用的发展、作用机制、手术步骤、有效性及安全性方面进行综述。
一、HIFU在青光眼应用的发展
HIFU在眼科应用的最早记录,是年Lavine等[7]将高强度超声聚焦于离体小牛眼的透明晶状体,导致白内障发生的报道,从而提出HIFU可以选择性破坏眼内特定组织的观点。随后,Purnell等[8]报道了首个HIFU应用于眼科领域的动物在体实验,其观察到HIFU导致视网膜脉络膜损伤以及局限性的睫状体破坏。基于这个研究结果,Rosenberg和Purnell[9]进一步使用HIFU对只兔子进行睫状体凝固术治疗后,观察眼压的变化以及睫状体的病理学改变,发现45%的治疗眼术后眼压显著下降,且眼压下降程度与超声治疗的剂量具有相关性,然而,48%的治疗眼出现了除睫状体外其他组织的永久性损伤。其后,Lizzi与Coleman的工程学与医学跨学科研究团队对HIFU在眼科的应用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在对HIFU造成的眼部损伤进行了深入研究后[10,11,12],重新设计了治疗探头(换能器)、超声能量及定位参数,并在年同时发表了2篇使用HIFU技术治疗青光眼及其疗效评估的论文[13,14]。其中1篇为动物实验研究,报道了86%的兔眼青光眼模型经HIFU治疗后眼压显著下降,且术后不同时间点的组织病理学实验表明,兔眼的治疗区域结膜完整、巩膜局部变薄、睫状体上皮局灶性萎缩,未见广泛性的组织破坏[13]。另1篇为临床研究,报道了69例晚期青光眼患者的HIFU治疗效果:在术后3个月的随访时间内,平均眼压从术前的40mmHg下降至17mmHg,其中83%患者的眼压降至25mmHg或更低,同时,并发症的发生率很低且主要为术后的葡萄膜炎[14]。基于Lizzi与Coleman的前期研究及后续的多中心临床研究[15,16,17,18,19],第1台HIFU治疗设备SonocareCST-(Sonocare公司,美国)于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用于治疗各种类型青光眼[20],不受患者的年龄、性别、种族、晶状体状态(有晶状体眼、无晶状体眼或人工晶状体眼)的影响。虽然HIFU技术在青光眼的治疗中取得了明显的疗效,但由于SonocareCST-的设计笨重、操作复杂,加上激光治疗技术的竞争,该设备在上市后的10年内逐渐被市场所淘汰。直到年,Aptel等[21]针对第1代产品的缺点,提出了HIFU治疗设备的全新设计,大大简化了HIFU睫状体凝固术的治疗流程,且通过兔眼的组织病理学实验,再次展现了HIFU睫状体凝固术的疗效及可控性[21,22]。这一新设计被迅速商品化成为EyeOP1青光眼治疗设备(EYETECHCARE公司,法国),分别于及年获得欧盟及中国的上市许可,用于青光眼的降眼压治疗,并将治疗术式命名为超声睫状体成形术(ultrasoundcycloplasty,UCP)。EyeOP1采用小型化的环形治疗探头,探头包含6个可以进行治疗的超声换能器,其工作频率为21MHz,声功率为2.00~2.45W,可将治疗区域组织的局部温度迅速升高至90℃。由于HIFU的第1代产品年代较为久远且已经停止生产,本文后续的内容主要针对第2代产品EyeOP1在青光眼治疗的临床应用。
二、HIFU治疗青光眼的原理
Aptel等[23]通过光学和电子显微镜观察兔眼HIFU治疗区短期及长期的组织形态学变化,提出HIFU治疗青光眼的双重原理。首先,HIFU产生的热量,会使睫状体的上皮及血管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从而减少房水的生成;其次,HIFU治疗后会在睫状体内、睫状体与巩膜之间以及脉络膜与巩膜之间产生液性腔隙,这些腔隙的范围与凝固性坏死组织的范围一致或稍大,腔隙内可见残余的组织隔断,同时,巩膜的变薄也是HIFU治疗后常见的组织学改变,这些改变都被认为会增加房水经葡萄膜巩膜途径的引流[23]。这些发现,也在其他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21,24,25,26]。然而,二者在HIFU降眼压治疗中的作用难以量化,目前尚无证据支持哪种原理是HIFU主要的治疗机制。由于2种机制作用于睫状体的不同部位,因此HIFU降眼压治疗最佳治疗靶点的选择,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UCP的手术步骤
在以往的研究报道中,均有UCP手术步骤及研究对象围手术期处理的简单介绍,其中Giannaccare等[27]发表的视频文章,最为详细地记录了使用EyeOP1治疗青光眼的步骤。UCP的术前准备,主要包括知情同意的签署、术眼的检查与治疗探头尺寸的计算。术前检查可以根据临床的需要进行增减,一般包括测量最佳矫正视力(视远及视近)、裂隙灯显微镜检查(联合房角镜检查前房角及前置镜检查眼底)、测量眼压、测量角膜横径(白到白距离)以及眼轴长度(角膜顶点至黄斑中心凹距离)。术前检查中的角膜横径及眼轴测量数值,将用于计算EyeOP1治疗探头的尺寸(治疗探头有3个尺寸,直径分别为11、12及13mm),目前此步骤的实施是将相关数据发送至设备生产商进行计算后以确定探头尺寸。术前局部抗生素及缩瞳治疗也可根据临床实际情况进行处方。治疗时患者取仰卧位,可将头部轻微后仰,使眼表保持水平位置。消毒铺巾前,根据情况选择球周浸润或球后阻滞麻醉,并按照操作说明开启EyeOP1治疗设备、输入患者信息、选择治疗扇区的数量(6、8及10个扇区,表1为源自设备生产商EYETECHCARE的不同探头尺寸及不同治疗扇区所对应的实际治疗范围)、连接治疗探头及定位环(配有集液器)。将定位环居中置入术眼,使角膜缘与定位环内界之间可见一均匀的宽度至少为2mm的巩膜环,确保定位环与眼表紧密接触,启动负压并通过系统检测。定位环内置入治疗探头并确保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定位环内注满常温的生理盐水。根据设备提示,踩下踏板启动治疗程序,治疗时嘱患者尽量保持不动,并确保定位环与眼表紧密接触。如术中出现紧急情况,可松开踏板,中断治疗。治疗程序的执行完全自动化,程序执行时的各个节点及操作提示将实时显示在设备屏幕上。治疗结束后,将定位环内的生理盐水吸入集液器,关闭负压,取出定位环及治疗探头。术眼滴抗生素及糖皮质激素滴眼液后纱布包扎。术后1h查看患者及测量眼压,根据情况处方抗生素滴眼液、糖皮质激素滴眼液及阿托品眼用凝胶,安排术后随访,患者可离院。术后随访时间点一般为术后1d、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及1年,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四、UCP治疗的有效性
截至年7月,共检索到17篇(中文与英文)国内外学者发表的UCP临床研究论文[24,25,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这些文献以难治性青光眼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只有4篇文献的研究对象包括未经治疗的青光眼患者[31,33,35,40]。由于EyeOP1第1代治疗探头可以选择HIFU治疗的时长(3、4及6s),而第2代治疗探头已经将治疗时长统一为8s;此外,在中国上市的设备,UCP治疗的范围可以在6、8及10扇区之间进行选择(未在国外学者文章中出现多于6扇区的UCP治疗),因此,本文将6扇区且每扇区8s的HIFU治疗作为标准治疗模式,以区分其他的治疗模式。
在使用6扇区HIFU治疗但涉及多种治疗时长(3、4、6及8s)且无法单独提取标准治疗模式相关数据的文章中[24,25,28,29,30,31,32,40],UCP降眼压的幅度在20.1%~40.8%,且眼压多在术后7d左右达到下降的最大幅度。Deb-Joardar和Reddy[36]报道了每扇区10s共6扇区的HIFU治疗结果,这也是目前文献中唯一采用治疗时长为10s的文章,其降眼压的幅度在术后12个月为30.4%,而该研究另一组接受标准治疗模式的患者,眼压下降幅度为37.4%。基于现有的文献,无法明确HIFU治疗时长与降眼压效果之间的关系。
在标准治疗模式[33,34,35,37,41,42]或可单独提取标准治疗模式相关数据[36]的文章中,UCP降眼压幅度范围在13.9%~45.0%。Graber等[37]报道了所有文献中最低的眼压降幅[眼压从基线的(23.0±6.8)mmHg降至(19.8±8.6)mmHg,降幅仅为13.9%],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该研究术后3个月及之后的失访率较高(47.1%~81.4%),术后12个月的随访率只有18.6%,因此结果的可靠性存在疑问。然而,Graber等[37]的文章是唯一比较了经巩膜睫状体激光光凝术(trans-scleralcyclophotocoagulation,TSCPC)与UCP降眼压效果的文献,虽然其结论是TSCPC降眼压的效果比UCP更佳,但由于研究设计为非随机对照,两组之间的样本量、基线眼压、随访率等参数差别显著,所以该研究的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国内学者杨丛丛等[38]与李博等[39]报道了10扇区且每扇区8s的HIFU治疗效果。杨丛丛等[38]用EyeOP1治疗了20例难治性青光眼(11例闭角型青光眼及9例继发性青光眼),术后3个月随访,两组的眼压分别从基线的(54.7±5.4)mmHg及(55.0±10.7)mmHg降至(19.6±6.9)mmHg与(26.6±12.5)mmHg。李博等[39]也治疗了40例难治性青光眼(20例闭角型青光眼及20例继发性青光眼),术后1个月随访,两组的眼压分别从基线的(54.3±4.6)mmHg及(54.3±4.5)mmHg降至(26.1±1.2)mmHg与(29.8±2.3)mmHg。与国外学者的文献[24,25,28,29,30,31,32,33,34,36,37,40,41,42]比较,国内学者文献[35,38,39]报道的研究对象基线眼压明显较高,因此相当一部分患者UCP术后随访的平均眼压仍会处于较高的水平,针对中国患者特点的UCP个性化治疗方案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共有5篇文献[28,29,30,31,33]报道了UCP的重复治疗情况,其中DeGregorio等[33]的文章报道了最多的重复治疗例数:在40例入选的受试者中,有20例(50%)在术后4个月接受了第2次UCP治疗;4个月后,在这20例接受了2次UCP治疗的患者中,又有12例(60%)接受了第3次UCP治疗以将眼压降至目标眼压。在接受了2次UCP治疗的20例患者中,与术前基线眼压相比,眼压下降幅度分别为18.1%及34.7%;在接受了3次UCP治疗的12例患者中,与术前基线眼压相比,眼压下降幅度分别为16.5%、32.7%、52.6%。该研究在术后12个月随访时的完全成功率(在不使用药物及不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条件下,5mmHg术后眼压≤21mmHg)为85%(34例),且术后使用降眼压滴眼液的数量显著减少。此外,Torky等[42]也报道了UCP术后使用降眼压滴眼液的数量显著减少,然而,综合所有报道了术前、术后用药数量的文献[28,29,30,31,32,33,34,36,40,42]来看,术后降眼压药物的数量并未见显著减少。
五、UCP治疗的安全性
从报道了并发症的文献[24,25,28,29,30,31,32,33,34,35,36,37,38,40,42]来看,UCP治疗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将这些文献报道过的所有并发症及发生例数综合分析后,UCP的术后并发症按照发生频率从高到低分别为:结膜充血(46.9%)、前房炎性反应(36.5%)、浅表点状角膜炎(17.7%)、结膜下出血(9.6%)、视力下降超过2行(5.8%)、角膜水肿(5.5%)、一过性眼压升高超过基线水平10mmHg(3.3%)、轻度瞳孔散大(2.0%)、低眼压(1.7%)、角膜溃疡(1.5%)及黄斑水肿(1.2%);几乎所有并发症在术后30d内自行或经治疗后恢复。此外,所有文献均未出现眼球萎缩的报道。
Pellegrini等[41]通过激光前房闪辉测试仪研究了UCP术后前房炎性反应的变化,发现前房闪辉检测值在UCP术后1d达到最高峰后逐渐下降,其水平维持在显著高于基线水平至术后1个月,而术后3个月及6个月的测量值则恢复至术前水平,因此提出如需重复UCP治疗,应至少在术后3个月后进行。Graber等[37]则比较了TSCPC与UCP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认为TSCPC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高于UCP,但基于前述的原因,这一结果仍需进一步验证。DeGregorio等[33]也认为UCP的重复治疗在增加成功率的同时,并未降低UCP治疗的安全性。
六、小结
HIFU在青光眼中的降眼压治疗展现了初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由于目前关于UCP的文献数量有限,且这些研究在设计、研究对象、入排标准、终点指标、分析方法、失访率及研究质量等方面的异质性明显,因此UCP在青光眼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仍需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加以证实。针对中国患者特点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希望对现有的证据进行总结,可以为UCP的临床应用提供一些参考。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nonkd.com/wadwh/11338.html